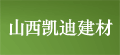全行業“勞務派遣”(包工制)被香港學者認為世界罕見。
這一現象又是產生于建筑行業層層轉包、層層墊資的生態鏈中。只要其中哪一個環節出問題,最后遭殃的都是最底層的農民工。
因此,制約或改善這一生態鏈,被認為是解決包工制的重要方向。
在一次一次的欠薪、工傷事件中,包工頭成了眾矢之的。在法律上并沒有明確地位的包工頭,事實上承擔了雇傭工人的工作。
2005年底,建設部發布了“3年之內取消包工頭”的號召。2007年10月,大連提出建立全國首個建筑業勞務基地,取消包工頭。
“實際上沒有根本好轉。”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律師時福茂根據他們辦理的上千件案件,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該工作站從2006年9月成立以來,就一直在呼吁取消包工頭制度。
在SACOM的報告里,中國特有的層層轉包制是農民工糟糕處境的體制之源。香港理工大學研究員陳敬慈認為,中國建筑(2.49,0.19,8.26%)業全行業的“勞務派遣”全世界都很罕見。
農民工權益受損的制度之源
已做“包工”近二十年的河北包工頭劉玉華(化名),解釋了導致建筑業農民工權益受損的重要“潛規則”。
在他看來,建筑業是由開發商主導的,讓誰來承建全憑開發商一句話。建筑公司那么多,惡性競爭難以避免。1997年以前,建筑商可以拿到5%到30%的“進場費”再開工;1997年以后,隨著競爭的加劇,相當多的建筑商開始墊資“進場”。而且除了總包,二包、包工頭也都要墊資。到包工頭,就要墊工人的生活費。
劉玉華將這種層層墊資稱為“扎錢”,“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建筑商害怕選錯開發商。碰到一個開發商是混蛋,就瞎了”。
在這樣奇特的生態鏈中,只要哪一個環節出問題,最后遭殃的都是最底層的農民工。“開發商將市場風險層層分解,最后到工人頭上分不下去了。”劉說。這樣的生態鏈也決定了建筑業將勞動力成本壓到最低,工人的生存條件差也就在所難免。
在劉玉華的職業生涯里,他有多次被開發商騙、被總包和二包涮,以及拖欠工人工資的經歷。如今,他名義上已不是“包工頭”,他也掛靠在某家勞務公司,承包勞務,但面臨的問題和以前并沒有多少不同。
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律師時福茂進一步介紹,不少勞務公司是皮包公司,仍然存在著向包工頭層層轉包的問題,“起訴勞務公司還不如起訴包工頭,法院還可以把欠薪的包工頭拘了”。
而根據SACOM的調查,從發包方到工人,層層轉包有的竟然多達六七層。
“勞動法離建筑行業太遠。”劉玉華說,法律規定的都是“紙上談兵”。比如工人工資按月發放問題,對他來說就很有點天方夜譚的味道。工人工資是含在承包款里的,總包、二包、包工頭不可能按月結算工程款,只能按工期結算。這種情況下,工人的工資怎么按月發?
第二,工人的工傷保險問題。工人流動性這么大,勞務公司只能按工程買保險,而沒法給每個人買。
第三,8小時工作制和加班工資問題。建筑業要搶工期,晚上不加班是不可能的。
全行業“勞務派遣”世界罕見
全國總工會民主與管理部部長郭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勞務派遣(即包工制)在整個中國都很不規范,建筑業尤為突出。
香港理工大學研究員陳敬慈長期研究中國勞動關系狀況。他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說,像中國這樣,建筑行業全行業采取勞務派遣制,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
包括香港以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大多采用固定工為主、臨時工為輔的用工體制。比如香港的建筑商,會按公司承包的工程量測算出大體需要多少骨干工人。這些工人是固定工,按月發薪。不足部分就從外面招零工。“如果沒有固定工人做保障,建筑公司根本沒有競爭力,攬不到工程。”
但是在中國內地,情況完全相反。根據他多年的調查和研究,現有的建筑公司大多從國有建筑公司脫胎而來。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為了擺脫固定工沉重的福利負擔,國有建筑公司幾乎全部轉為包工制,建筑工人也從國有企業的固定職工變為打零工者。包工制也分兩種,一是承包制,公司只養管理人員,將勞務轉包出去;二是“掛單”制,只要繳納管理費,沒有資質的建筑單位也可以掛靠。這樣就導致建筑商離實際干活兒的工人很遠,雇傭關系不清晰、不穩定,工人的工資、福利保障無從談起。
在中國的建筑業市場中,缺乏多種制衡力量,導致該行業畸形發展。比如沒有行規的約束。建筑商墊資“進場”,法律雖然不禁止,但是在行業協會發育充分的國家,會排斥這種惡性競爭。第二,工人無法借助工會組織,集體與資方談判。單個的農民工在勢力強大的資方面前毫無議價能力。
陳認為,尤其是在金融危機之下,農工民失業加重,談判能力降低,欠薪等情況更易發生。
建筑業的“包工制”該往何處去?和陳敬慈傾向于建筑商直接用工不同,郭軍說,不能違背這個行業流動性很大的規律。他認為有兩個方向,一是把包工隊變成勞務派遣公司,規范包工頭用工;二是成立專業的勞務分包公司。一些大的建筑商一年會用四五千名工人,他們已經和勞務分包公司有固定的合作。兩種方式都能保證農民工和用人單位形成固定的勞動關系。
陳敬慈認為,在規范勞動關系上,立法上還有作為。比如可以規定從發包方到工人,承包關系不能超過3層。這種做法是香港和國外很多國家選用的。其次,建筑工人是技術工人,經過職業培訓后持證上崗。在香港等地,他們比其他工人更有自豪感。這和中國內地建筑工人完全無培訓的情況很不相同。“國家對建筑業用工應該有個規劃,而不是設想他們將來會回到農村,完全不給予他們任何保障。”陳敬慈說。
這一現象又是產生于建筑行業層層轉包、層層墊資的生態鏈中。只要其中哪一個環節出問題,最后遭殃的都是最底層的農民工。
因此,制約或改善這一生態鏈,被認為是解決包工制的重要方向。
在一次一次的欠薪、工傷事件中,包工頭成了眾矢之的。在法律上并沒有明確地位的包工頭,事實上承擔了雇傭工人的工作。
2005年底,建設部發布了“3年之內取消包工頭”的號召。2007年10月,大連提出建立全國首個建筑業勞務基地,取消包工頭。
“實際上沒有根本好轉。”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律師時福茂根據他們辦理的上千件案件,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該工作站從2006年9月成立以來,就一直在呼吁取消包工頭制度。
在SACOM的報告里,中國特有的層層轉包制是農民工糟糕處境的體制之源。香港理工大學研究員陳敬慈認為,中國建筑(2.49,0.19,8.26%)業全行業的“勞務派遣”全世界都很罕見。
農民工權益受損的制度之源
已做“包工”近二十年的河北包工頭劉玉華(化名),解釋了導致建筑業農民工權益受損的重要“潛規則”。
在他看來,建筑業是由開發商主導的,讓誰來承建全憑開發商一句話。建筑公司那么多,惡性競爭難以避免。1997年以前,建筑商可以拿到5%到30%的“進場費”再開工;1997年以后,隨著競爭的加劇,相當多的建筑商開始墊資“進場”。而且除了總包,二包、包工頭也都要墊資。到包工頭,就要墊工人的生活費。
劉玉華將這種層層墊資稱為“扎錢”,“男怕入錯行,女怕嫁錯郎,建筑商害怕選錯開發商。碰到一個開發商是混蛋,就瞎了”。
在這樣奇特的生態鏈中,只要哪一個環節出問題,最后遭殃的都是最底層的農民工。“開發商將市場風險層層分解,最后到工人頭上分不下去了。”劉說。這樣的生態鏈也決定了建筑業將勞動力成本壓到最低,工人的生存條件差也就在所難免。
在劉玉華的職業生涯里,他有多次被開發商騙、被總包和二包涮,以及拖欠工人工資的經歷。如今,他名義上已不是“包工頭”,他也掛靠在某家勞務公司,承包勞務,但面臨的問題和以前并沒有多少不同。
北京市農民工法律援助工作站律師時福茂進一步介紹,不少勞務公司是皮包公司,仍然存在著向包工頭層層轉包的問題,“起訴勞務公司還不如起訴包工頭,法院還可以把欠薪的包工頭拘了”。
而根據SACOM的調查,從發包方到工人,層層轉包有的竟然多達六七層。
“勞動法離建筑行業太遠。”劉玉華說,法律規定的都是“紙上談兵”。比如工人工資按月發放問題,對他來說就很有點天方夜譚的味道。工人工資是含在承包款里的,總包、二包、包工頭不可能按月結算工程款,只能按工期結算。這種情況下,工人的工資怎么按月發?
第二,工人的工傷保險問題。工人流動性這么大,勞務公司只能按工程買保險,而沒法給每個人買。
第三,8小時工作制和加班工資問題。建筑業要搶工期,晚上不加班是不可能的。
全行業“勞務派遣”世界罕見
全國總工會民主與管理部部長郭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勞務派遣(即包工制)在整個中國都很不規范,建筑業尤為突出。
香港理工大學研究員陳敬慈長期研究中國勞動關系狀況。他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說,像中國這樣,建筑行業全行業采取勞務派遣制,在全世界都是罕見的。
包括香港以及大多數國家和地區大多采用固定工為主、臨時工為輔的用工體制。比如香港的建筑商,會按公司承包的工程量測算出大體需要多少骨干工人。這些工人是固定工,按月發薪。不足部分就從外面招零工。“如果沒有固定工人做保障,建筑公司根本沒有競爭力,攬不到工程。”
但是在中國內地,情況完全相反。根據他多年的調查和研究,現有的建筑公司大多從國有建筑公司脫胎而來。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為了擺脫固定工沉重的福利負擔,國有建筑公司幾乎全部轉為包工制,建筑工人也從國有企業的固定職工變為打零工者。包工制也分兩種,一是承包制,公司只養管理人員,將勞務轉包出去;二是“掛單”制,只要繳納管理費,沒有資質的建筑單位也可以掛靠。這樣就導致建筑商離實際干活兒的工人很遠,雇傭關系不清晰、不穩定,工人的工資、福利保障無從談起。
在中國的建筑業市場中,缺乏多種制衡力量,導致該行業畸形發展。比如沒有行規的約束。建筑商墊資“進場”,法律雖然不禁止,但是在行業協會發育充分的國家,會排斥這種惡性競爭。第二,工人無法借助工會組織,集體與資方談判。單個的農民工在勢力強大的資方面前毫無議價能力。
陳認為,尤其是在金融危機之下,農工民失業加重,談判能力降低,欠薪等情況更易發生。
建筑業的“包工制”該往何處去?和陳敬慈傾向于建筑商直接用工不同,郭軍說,不能違背這個行業流動性很大的規律。他認為有兩個方向,一是把包工隊變成勞務派遣公司,規范包工頭用工;二是成立專業的勞務分包公司。一些大的建筑商一年會用四五千名工人,他們已經和勞務分包公司有固定的合作。兩種方式都能保證農民工和用人單位形成固定的勞動關系。
陳敬慈認為,在規范勞動關系上,立法上還有作為。比如可以規定從發包方到工人,承包關系不能超過3層。這種做法是香港和國外很多國家選用的。其次,建筑工人是技術工人,經過職業培訓后持證上崗。在香港等地,他們比其他工人更有自豪感。這和中國內地建筑工人完全無培訓的情況很不相同。“國家對建筑業用工應該有個規劃,而不是設想他們將來會回到農村,完全不給予他們任何保障。”陳敬慈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