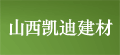曾經,一些以勞動密集型企業起家的城市被冠上靠“斷指經濟”發展的帽子。對于1.2億中國農民工來說,他們在城市中安身立命的最大資本就是他們健康的身體,但事實上由于置身建筑、礦山等高危行業,由于崗前培訓的缺乏、工作環境的惡劣等等原因,他們健康的身體最容易受到威脅。而這些脆弱的身體支撐的是同樣脆弱的中國內地幾千萬農民家庭的生計,是孩子們的課本,是老人的贍養。
今年2月7日,國務院正式印發《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簡稱“國發五號文”)。這是1949年以來第一份專門解決農民工問題的國務院文件,也是迄今為止中國政府關于農民工問題的最高規格的文件。在這個長達9300字的文件中,農民工的社會保障被放到了重要位置,要求優先解決農民工工傷保險和大病醫療保障。
去年,廣州率先實行農民工可以單獨參加工傷保險的政策。據廣州市勞動部門提供的數字,目前廣州市有170萬農民工參加工傷保險,仍有相當多的農民工處于無保障的位置,即使是購買了工傷保險的農民工也不得不時常面對煩瑣的工傷認定和勞動仲裁。
在廣州農民工中,阿毛是非常普通的一個,從蹲在醫院的墻角等著搬運水泥開始,34歲的他已經在廣州打工10年。和大部分農民工一樣,壯實的身體是阿毛最大的本錢,他從來不生病,一年到頭只會感冒一兩次,吃兩片最便宜的感冒藥就好了。直到半個月前,他修理住處的一扇破門時,新買來的電鋸從他的左手斜切了過去,“手一下子就像脫了骨的雞爪一樣”,4只手指斷了,只剩下一層皮連接。
發生意外的時候,阿毛是一家叫做三川智傳的公司工程部的員工,每天的工作就是搭建各種各樣的舞臺和背景板,手是他工作最重要的資本。他坐著摩托車被就近送到了廣州市第六人民醫院。第一個醫療決定是截肢,整個費用大約3000多元。這時,下海前從事中醫骨科的公司董事長程敏說了“不”,他通過以前的朋友,聯系了和平手外科醫院,快速轉院后,經過5個小時的手術,4只斷指接上了。
昨天下午,記者在病房里見到了坐在床上的阿毛。他的精神狀態不錯,手術恢復得很好,但左手斷指的部分還被層層紗布包裹著。到昨天為止,手術的整個費用已經上升到3萬多元,所有的錢都是作為私營企業主的程敏支付的。
“可能我一直當醫生吧,我知道手對于一個人來說意味著什么。截肢很簡單,而且只需花費兩三千塊錢,但是手是用來創造財富的。阿毛是他們家的支柱,在湖南老家上有老人,下有兩個小孩,他沒有了手,一家人的日子怎么過?”程敏的話讓鄰床的農民工都動了容。
在這家專業的手外科醫院,醫生們接觸最多的就是手部創傷,主治醫生陳錦濤告訴記者:“雖然技術已經有很大進步,但斷指再接手術必須在6個小時內做才能保證存活。很多農民工其實是因為種種原因錯過了最佳時間而殘廢。”而醫院的負責人吳洪波告訴記者:“我們經常見到一些老板和打工仔因為費用問題發生糾紛吵架。”
跟包工頭14年未享工傷險
阿毛可以說是比較幸運的一個農民工。40歲的張福元已經被工傷困擾了8個月,但事情似乎還遠遠沒有到盡頭。
目前,張福元的右眼已經基本看不見了,夫妻倆在在南海打工的老鄉那里借住,他已經無力支付呆在廣州的生活費用,靠老婆做小工每天賺的25元維持著生活,接下來等待他們的還有漫長的勞動仲裁,甚至民事訴訟。在湖南零陵的農村,兩個孩子正等著他們寄錢回去交新學年的學費,而他的老母親因為他的意外整天以淚洗面。
張福元不愿意回憶那一天,去年11月26日,在珠江俊園的工地上,在打混凝土的時候,一個尖利的錐子頭刺進了他的右眼。這是他1990年出來打工后第一次遇到這么嚴重的傷害。雖然他記得自己曾經填過身份證號碼,工資單里也扣過160元錢,但勞動部門的登記顯示,老板并沒有給他購買工傷保險,雖然他已跟了這個包工頭14年。
張福元被送到了廣州郵電醫院,動了四個半小時的手術,總共花了6000元,因為事關眼睛,他一直要求轉院到中山大學附屬眼科醫院。10天之后,張福元出院了,他一直認為自己是被包工頭騙出院的,因為包工頭跟他說先辦出院才能轉院,但等他辦了出院后,包工頭也沒有出錢讓他再住院。
此后,張福元一直以門診的方式看眼睛,到現在總費用已經差不多花了兩萬元,其中老板出了一萬八千元后就再也不愿意出錢了。除了兩千元醫藥費外,張福元更關心的是自己今后的生活,醫生告訴他,他的右眼病情已經穩定了,不可能再有好轉,如果他繼續干重活,汗水流入眼睛,也會感染到左眼。殘疾是一定的了,將來的生活怎么辦呢?
認定工傷賠償要過11道關
張福元想到了勞動部門,他到勞動部門申請工傷認定。6月1日,鑒定的結果出來,他被認定為7級傷殘,根據一系列復雜的計算,加上賠償和生活費補償,他應當可以得到近8萬元,這筆錢要由老板來支付,但與老板的協商并沒有結果,所以為了拿到這筆賠償,他下一步要進行的是勞動仲裁。
張福元的維權路將是漫長的。據中國工傷損害賠償網的站長黃樂平計算,正常情況下(不含強制執行),在法定時效內走完工傷維權所有程序需要1286天(約3年半),如果用人單位存心設置障礙,這個時間可能長達1932天(5年多)。“讓最弱的群體去接受如此煩瑣的程序,這就是工傷認定制度和勞動仲裁制度的尷尬。”黃樂平說。
“工傷爭議大都發生在勞動管理不規范的用人單位,這些用人單位一般沒有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雙方之間形成的是一種事實勞動關系,而且這些用人單位不會讓勞動者參加工傷保險,但發生工傷事故后,用人單位則必須按照參加工傷保險企業標準進行賠償。在是否存在勞動關系?是否因工作而受傷?受傷程度如何?這些問題上往往引發爭議。”熟悉工傷爭議和仲裁的人士說。
按照工傷法規定,企業老板雖然沒有給農民工購買工傷保險,但是只要存在事實勞動關系,老板就必須按照工傷規定,自己掏腰包,支付農民工相應賠償。“因此,如果農民工想打贏官司拿到錢,起碼要經過11道關。”
很多農民工考慮到這一漫長過程,最終只有放棄,選擇和企業私了。
建筑老板買工傷保險有貓膩
“從全國范圍來看,勞動保障系統中的行政訴訟和行政復議案例中,九成和工傷爭議有關。在廣州,這一數字也在五成左右。”廣州市勞動保障局工傷保險處陳泰才處長說,工傷爭議在勞動爭議中占著絕對數量。
“按照規定,用人單位需要給勞動者購買工傷保險,并且保險費用由企業支付。”陳泰才說,由于工傷保險繳費率只占職工工資1%左右,一名農民工一年費用算下來也就200元左右。“但就是如此低的繳費,也有企業不愿意繳納。”
“我們工地上一共有200多名工人,但是老板只是向勞動部門買了10份工傷保險。如果沒有參加工傷保險的工人出了事故,老板就會讓這名工人改名,改成已經買了工傷保險的工人名字,然后就可以騙取到工傷保險。”昨天,海珠區東曉南路一工地上的工人張明德接受記者采訪時說,老板曾經告誡過他們,不準向外人透露這個建筑行業的工傷參保秘密。
工人冒名頂替領賠償
張明德已經在這個工地上干了一年多,由于建筑工人流動性十分頻繁,老板沒有和他們這些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其間他親眼看到一名在工地上僅僅干了10天的工人出事,從4樓摔到地上,在醫院搶救3個月,花了30多萬元,最終保命,但是頸椎以下全部癱瘓,后來,這名來自四川的工人在得到建筑老板30萬元賠償后,離開了工地。
“我們都知道,這名工人是頂替另外一名參加了工傷保險的工人名字,才獲得工傷賠償的。”張明德說,他已經在珠三角多個建筑工地上干過,“老板都是這樣操作的。”
不僅建筑行業如此,包括采礦和運輸等多個工傷高危行業,很多也是如此操作:不管有多少工人,只是購買幾份工傷保險,一旦有工人出事,就立即讓這名工人換成參加工傷保險的工人名字騙保。
企業不愿讓工傷者久住醫院
記者從知情人士處獲悉,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在員工發生工傷后,往往會和醫院達成協議:盡量用便宜的藥,一旦工人病情穩定后,就立即將病人從醫院趕走。“因為現在藥費很貴,動輒上萬元甚至幾十萬元,哪個企業都墊不起。”張明德說,那位被摔成高位癱瘓的四川農民工,就是如此經歷。
“由于摔倒地上人已經昏迷不醒,老板怕弄出人命,因此當時就送到海珠區一家三甲醫院搶救,花了20多萬元,后來看見不會死人,立即就把這名工人轉到崗頂附近一家醫院,藥費立即就降下來了。治療了幾天后,醫院說企業沒有交錢,順理成章地就把這名病人趕出醫院,老板馬上叫人把這名工人抬到一間出租房里,不再繼續治療。”
廣州率先實行單獨參保工傷險
“出了工傷一到醫院看病就要錢,一些實力不強的企業,當然不愿意支付這筆費用,因此企業老板會選擇和工人私了,不選擇治療,而是一次性賠償萬兒八百的。”在白云區某鞋廠打工被機器奪去3只手指的劉向英說,老板不準她去大醫院,而是到附近城中村里一個診所進行包扎了事,然后威脅她,一旦到勞動部門舉報,就一分錢都別想拿到。“那個診所已經成了鞋廠的‘定點醫療機構’,早就和老板達成過協議。”
去年,廣州在全國率先實行農民工可以單獨參加工傷保險的政策。今年6月26日,廣州市勞動保障局再次發出通知,要求用人單位為與之建立勞動關系而尚未參加社會保險的農民工先行參加工傷保險。
一名工人參加工傷保險,企業一年只需要出200元左右,但是如果出了工傷后,治療和工傷補助往往上萬元。陳泰才表示,企業為農民工買保險不僅僅獲得經濟利益,更是一種社會責任。